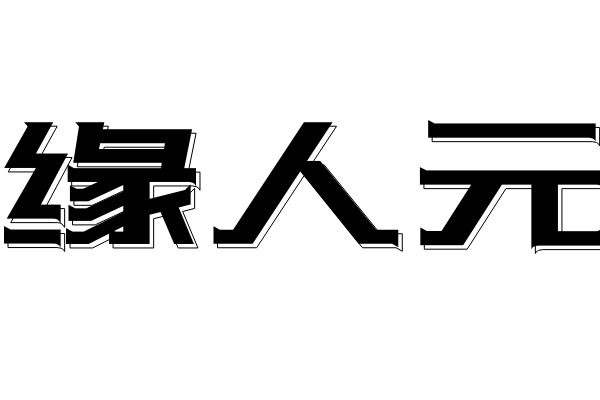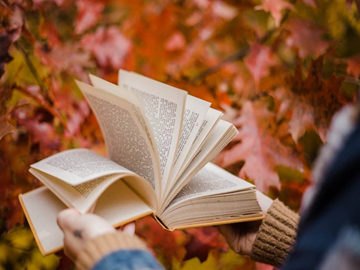口味谁都有,想法各不同,可习惯却难以改变。从我父辈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,到今天我也已六旬有余。我见证了这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变,也经历了自己从孩童到大人的千变万化。但有一样东西,始终没有改变,那就是我对于“吃”的执着。
第一节:我眼中的美食家庭
家中有六口人,父母、叔婶、我和妹妹。原本的一栋三间小屋,还要分出两扇半门的厨房—供一个姑娘家傍晚做饭。这个经历,在情感上,让我感受到了关于饭桌的重要性:无论身处何方,饭桌都是人类情感不可或缺的核心位置。每日的早中晚,我们会围坐在一起,争斤斗量饭菜的滋味成了人们之间最真挚的交流方式。于是,我便养成了自己做饭的兴趣。
第二节:我年少的爱情,和“归家”的意义
25岁,那年我在陕西一个小城市的电报局工作,年轻又爱自由的我,选择远赴他乡打工。工作辛苦,但却不好找。好消息是,这正巧让我遇到了我家OG新锐的身影,他给了我梦幻中的安全感和归宿感。于是千里迢迢,我模糊了我的梦想,选择了“嫁”给了这个家庭,安安稳稳地开始了我的“返乡潮”人生。嫁到农村这个新环境,让我最受感染的倒是他们的乡土味,这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“家”的本质,这个值得我“回归”的标志。
第三节:我的亲子故事——陕西乡村的“养娃”生态
生育母亲的经历,让我脱胎换骨。在陕西这样一个地方,大家对于“养娃”的概念,很多人会将之等同于给这个孩子不断增长的“生命体力”提供保障而已。但是,这隐藏了岛国父母陷入的生活困境:孩子的成长给了他们繁重的育儿任务,但同时又似乎让他们收获的不到什么实质上的“爱”的力量。当我孩子已经是青春年少的时候,我也意识到,爱与养育学习的平衡非常重要。陪伴孩子,是我这个时代的父母们的权利和义务。
时间和风尘让我的内心变得坚强而成熟,但我的饮食品味还是保留了 四六十年代的文人气质:美食、诗歌、与心上人共度温情时光。吃是生活,也是我人生中的常数。像一件携带记忆的习性,像一件手摸、舌舔的亲密贴身。这既是我的一个看似简单而基本的行为习惯,也是一个物化了我丰富生命经验的一片正面面貌。过去的味道,很多时候是“露头即满足”的,是美好生活的象征。而此刻,饭桌上,一家人聚在一块,说说笑笑,满足、重要的是人情味,我们的生活既有了温暖,也被寄托了回忆。